
《繫年》簡49“![]() ”字結構小考
”字結構小考
(首發)
偉盈
第八章“秦穆公欲與楚人為好,![]() (焉)
(焉)![]() (脫)
(脫)![]() (申)公義(儀),囟(使)
(申)公義(儀),囟(使)![]() (歸)求成。秦
(歸)求成。秦![]() (焉)【四八】
(焉)【四八】![]() (始)與晉
(始)與晉![]() (執)
(執)![]() (亂/怨),与(與)楚爲好
(亂/怨),与(與)楚爲好![]() 。【四九】”整理者說:
。【四九】”整理者說:
![]() ,從行,
,從行,![]() 聲🐈,讀爲“亂”💂🏼♀️。“執亂”與“爲好”相對,義當近於“執讎”💼。《國語.越語上》“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,而又與大國執讎”,韋注:“執🤽🏿♀️,猶結也👰🏽♀️。”《魯語上》“亂在前矣”🤌,注:“亂,惡也。”是執亂猶云結惡。[1]
聲🐈,讀爲“亂”💂🏼♀️。“執亂”與“爲好”相對,義當近於“執讎”💼。《國語.越語上》“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,而又與大國執讎”,韋注:“執🤽🏿♀️,猶結也👰🏽♀️。”《魯語上》“亂在前矣”🤌,注:“亂,惡也。”是執亂猶云結惡。[1]
此說可從。簡93有“![]() ”字作
”字作![]() 🤵🏼♂️,但是簡49的“亂”爲什麼寫作從“行”旁👩🦯📺?筆者以爲“行”旁應該是由“
🤵🏼♂️,但是簡49的“亂”爲什麼寫作從“行”旁👩🦯📺?筆者以爲“行”旁應該是由“![]() ”、“
”、“![]() ”演變而來👨❤️👨。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四)·采風曲目》簡1有一個曲目名“埜(野)又(有)葛”🖖,“葛”字寫作🎪:
”演變而來👨❤️👨。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四)·采風曲目》簡1有一個曲目名“埜(野)又(有)葛”🖖,“葛”字寫作🎪:
![]()
中間從“![]() ”,是由“
”,是由“![]() ”演變而來。三體石經《春秋》僖公人名“介葛盧”之“葛”字作如下之形🌲:
”演變而來。三體石經《春秋》僖公人名“介葛盧”之“葛”字作如下之形🌲:
![]()
陳劍先生已指出“![]() ”,是由“
”,是由“![]() ”形中部筆畫斷裂🦵、左右兩筆又引長下垂演變而來🪞。[2]此外“葛”還有如下的寫法🗃🧜🏼:
”形中部筆畫斷裂🦵、左右兩筆又引長下垂演變而來🪞。[2]此外“葛”還有如下的寫法🗃🧜🏼:
(1) ![]() (《璽彙》2263)
(《璽彙》2263) ![]() (《璽彙》2264)
(《璽彙》2264)
(2)![]() (《上博(三)·周易》簡43)
(《上博(三)·周易》簡43)
(3)![]() (《季康子問於孔子》簡8)
(《季康子問於孔子》簡8)
施謝捷🦞、陳劍先生都已指出“葛”字中間所從與“索/素”字形相近✤。郭永秉、鄔可晶先生進一步指出:
“葛”字作![]() 🏌️♂️👰🏼♀️,可能應當跟本文所論“
🏌️♂️👰🏼♀️,可能應當跟本文所論“![]() ”字聯繫起來考察。“
”字聯繫起來考察。“![]() (割)”💂♀️、“葛”古音全同,甲骨卜辭作爲地名的“
(割)”💂♀️、“葛”古音全同,甲骨卜辭作爲地名的“![]() (割)”可能當讀爲“葛”🤒,如果上文所論“
(割)”可能當讀爲“葛”🤒,如果上文所論“![]() (割)”字可能兼以“索”旁表音這一點基本符合事實的話,那麼戰國文字及傳抄古文“葛”以“索”爲聲旁也就並不顯得奇怪了🛌🏿🤸🏽。作出這樣的解釋,跟陳劍先生所推測的🦹🏼♀️,“用‘索’👨🚀、‘艸’兩字會意(‘索’或變作‘素’),從‘可爲繩索之草’的角度來表示‘葛’🪄,或者說由此來‘提示’人們想到‘葛’”的可能性並不互相排斥🏌🏼,也就是說⚅,此字可能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會意兼形聲字。當然🏄🏼,事實也許還有另一種可能,即戰國文字和三體石經古文的“葛”字,實爲从“
(割)”字可能兼以“索”旁表音這一點基本符合事實的話,那麼戰國文字及傳抄古文“葛”以“索”爲聲旁也就並不顯得奇怪了🛌🏿🤸🏽。作出這樣的解釋,跟陳劍先生所推測的🦹🏼♀️,“用‘索’👨🚀、‘艸’兩字會意(‘索’或變作‘素’),從‘可爲繩索之草’的角度來表示‘葛’🪄,或者說由此來‘提示’人們想到‘葛’”的可能性並不互相排斥🏌🏼,也就是說⚅,此字可能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會意兼形聲字。當然🏄🏼,事實也許還有另一種可能,即戰國文字和三體石經古文的“葛”字,實爲从“![]() (割)”省聲的一個字,其文字結構類型與从“刪”省聲的“珊”、“姍”✢、“柵”字非常類似🙆🏻♂️。究竟上述哪一種解釋較合事實,有待進一步研究🥴。[3]
(割)”省聲的一個字,其文字結構類型與从“刪”省聲的“珊”、“姍”✢、“柵”字非常類似🙆🏻♂️。究竟上述哪一種解釋較合事實,有待進一步研究🥴。[3]
“索”可作![]() (師克盨蓋🧝🏻♀️,《集成》4468)
(師克盨蓋🧝🏻♀️,《集成》4468)![]() (師克盨(蓋),《集成》4467),添加“
(師克盨(蓋),《集成》4467),添加“![]() ”形筆畫🧶。燕國璽印作
”形筆畫🧶。燕國璽印作![]() (《璽彙》3898)、秦印作
(《璽彙》3898)、秦印作![]() (《戰國文字編》388頁)、秦簡作
(《戰國文字編》388頁)、秦簡作![]() (睡日乙簡一八四·15)、
(睡日乙簡一八四·15)、![]() (《睡虎地‧秦律十八種》22)、
(《睡虎地‧秦律十八種》22)、![]() (
(![]() 🦛,《嶽麓一‧爲吏》六八正叄),將“
🦛,《嶽麓一‧爲吏》六八正叄),將“![]() ”筆畫延長爲“冂”形。[4]所以“葛”字(1)形所從的“冂”應該也是“
”筆畫延長爲“冂”形。[4]所以“葛”字(1)形所從的“冂”應該也是“![]() ”演變而來。[5]“糸”旁兩邊所加的四小斜筆當是裝飾符號🤵🏽,如底下諸字[6]4️⃣:
”演變而來。[5]“糸”旁兩邊所加的四小斜筆當是裝飾符號🤵🏽,如底下諸字[6]4️⃣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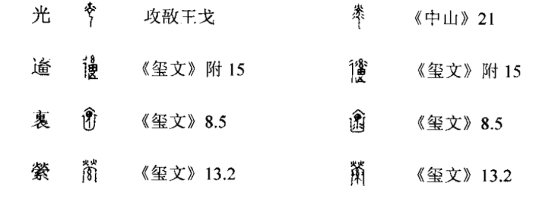
(2)、(3)形是(1)形的進一步簡省🦫,字形演變與“縈”相似,陳劍先生已經說的很清楚了。《說文》小篆“索”作![]() 🤳,分析其形爲“从
🤳,分析其形爲“从![]() 👨🏼🏭、糸”。此說不可從🕵🏻♀️,施謝捷先生指出,此形“實係古文字中‘索’異構‘
👨🏼🏭、糸”。此說不可從🕵🏻♀️,施謝捷先生指出,此形“實係古文字中‘索’異構‘![]() ’的訛變之形”🧓🏼。[7]也就是“冂”形的裂解🧔🏿♂️。《說文》還有“
’的訛變之形”🧓🏼。[7]也就是“冂”形的裂解🧔🏿♂️。《說文》還有“![]() ”字作
”字作![]() ☮️,所從的“索”旁在“糸”旁兩邊加上兩小斜筆爲飾筆。
☮️,所從的“索”旁在“糸”旁兩邊加上兩小斜筆爲飾筆。
“胤”字的演變過程與“素/索”、“葛”📟🦡、“縈”等字相似,其字形如下:
(4)![]() (
(![]() 簋4075)
簋4075)
(5)![]() (秦公鐘)
(秦公鐘)![]() (晉公盆)
(晉公盆)
(6)![]() (
(![]()
![]() 壺)
壺)
(7)![]() (說文古文胤)
(說文古文胤)
(8)![]() (《周易》49)
(《周易》49)
對於《周易》的寫法,濮先生說👟:“‘![]() ’,疑‘胤’字👎🏽🎏。《說文·肉部》:‘胤,子孫相承續也。從肉🎯、從八,象其長也,從
’,疑‘胤’字👎🏽🎏。《說文·肉部》:‘胤,子孫相承續也。從肉🎯、從八,象其長也,從![]() 🥩,象重累也。’許慎所謂從‘八’🖐🏽,疑從‘行’省🙂↔️。”[8]季旭昇先生則認爲🧖🏽♀️:此字從“行”、“胤”聲🧙🏼♂️,讀爲“胤”🎒,可從。此字中間所從當即“胤”字本形,字從“肉”🧑🏼💼,表示骨肉血胤,從“ㄠ”表示子孫綿延🤙🏿,或作“胤”🛅,旁邊的筆畫原是“ㄠ”旁的飾筆,不得釋爲“行省”。[9]其說可從👰🏽♂️。《說文》小篆的“八”形是繼承春秋早期的秦公鐘而來,不會是從楚簡《周易》的“行”旁省簡而來。張富海先生指出《說文》古文的寫法是揉合(5)🤾🏿♂️、(6)兩種形體。上博簡《周易》49號簡“胤”作
🥩,象重累也。’許慎所謂從‘八’🖐🏽,疑從‘行’省🙂↔️。”[8]季旭昇先生則認爲🧖🏽♀️:此字從“行”、“胤”聲🧙🏼♂️,讀爲“胤”🎒,可從。此字中間所從當即“胤”字本形,字從“肉”🧑🏼💼,表示骨肉血胤,從“ㄠ”表示子孫綿延🤙🏿,或作“胤”🛅,旁邊的筆畫原是“ㄠ”旁的飾筆,不得釋爲“行省”。[9]其說可從👰🏽♂️。《說文》小篆的“八”形是繼承春秋早期的秦公鐘而來,不會是從楚簡《周易》的“行”旁省簡而來。張富海先生指出《說文》古文的寫法是揉合(5)🤾🏿♂️、(6)兩種形體。上博簡《周易》49號簡“胤”作![]() 🧒🏽,從“行”形🫃🏽,與此古文比較接近👨🏿🔬。[10]此說亦有理👳🏼,則(7)與(8)當存在演變的關係,依照這種演變關係,我們可以推斷“葛”或“索/素”所从的“
🧒🏽,從“行”形🫃🏽,與此古文比較接近👨🏿🔬。[10]此說亦有理👳🏼,則(7)與(8)當存在演變的關係,依照這種演變關係,我們可以推斷“葛”或“索/素”所从的“![]() ”當有可能演變爲“行”形🧗♀️。事實上這種寫法確實存在,《馬王堆帛書‧德聖》:“經者,至
”當有可能演變爲“行”形🧗♀️。事實上這種寫法確實存在,《馬王堆帛書‧德聖》:“經者,至![]() 〈素〉至青(精),何以能爲者
〈素〉至青(精),何以能爲者![]() □□□廣□
□□□廣□![]() 8/459”注釋云:
8/459”注釋云:
“![]() ”,原釋文釋爲“率”🎅🏼,(《馬[壹]》39頁)此據原形隸定。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(1974🧚🏼🔀:25)釋爲“
”,原釋文釋爲“率”🎅🏼,(《馬[壹]》39頁)此據原形隸定。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(1974🧚🏼🔀:25)釋爲“![]() ”💁。近是🔏。原注:“帛書《經法·道法》:‘至素至精👩🏽🦰🛟,浩彌無形’(九行上)。此文‘率’字當讀爲‘素’🟨。”(《馬[壹]》39頁注[七])今按:“
”💁。近是🔏。原注:“帛書《經法·道法》:‘至素至精👩🏽🦰🛟,浩彌無形’(九行上)。此文‘率’字當讀爲‘素’🟨。”(《馬[壹]》39頁注[七])今按:“![]() ”字除去“行”的部分🌍,與“素”相似,此“
”字除去“行”的部分🌍,與“素”相似,此“![]() ”也可能即“素”之形誤🤳。[11]
”也可能即“素”之形誤🤳。[11]
其說可從😕。帛書字形作![]() 👮🏽♂️,比對《五行》“索”207行作
👮🏽♂️,比對《五行》“索”207行作![]() ,其“行”旁是由“
,其“行”旁是由“![]() ”逐步演變而來。即:
”逐步演變而來。即:
![]() →
→![]() →
→![]() →
→![]() 。
。
回頭來看《繫年》的“亂”字由![]() 演變成
演變成![]()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《郭店·老子甲》簡26“亂”作
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《郭店·老子甲》簡26“亂”作![]() ,在“幺”旁所加的兩直筆亦可能是由“
,在“幺”旁所加的兩直筆亦可能是由“![]() ”演變而來,如同上舉的《說文》
”演變而來,如同上舉的《說文》![]() 字🏋🏿♀️。不過,我們知道“
字🏋🏿♀️。不過,我們知道“![]() ”亦偶有不加“
”亦偶有不加“![]() ”形的寫法🚕💆♂️,如伊簋“
”形的寫法🚕💆♂️,如伊簋“![]() ”作
”作![]() 🚈,蔡侯
🚈,蔡侯![]() 鐘作
鐘作![]() 🧗♀️,蔡侯
🧗♀️,蔡侯![]() 食鼎作
食鼎作![]() ↗️,[12]則《老子》的字形也可能是繼承蔡侯
↗️,[12]則《老子》的字形也可能是繼承蔡侯![]() 食鼎的“
食鼎的“![]() ”旁,而後在“幺”旁加兩直筆爲飾👲🏽,如同“胤”的(5)形。《說文》卷四下
”旁,而後在“幺”旁加兩直筆爲飾👲🏽,如同“胤”的(5)形。《說文》卷四下![]() 部“
部“![]() ”字古文作
”字古文作![]() ,所從“冂”形也是由“
,所從“冂”形也是由“![]() ”演變而來,如同上列秦簡的
”演變而來,如同上列秦簡的![]() 字。
字。
[1] 李學勤主編🤦🏿♂️: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貳)》第156頁注5,中西書局2011年👩🚀👈🏻。
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279。又載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8輯第68~70頁,大象出版社2007年🧇、氏著:《戰國竹書論集》第183-188頁🫘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。
[3] 郭永秉🔘、鄔可晶:《說“索”👨🦽➡️、“![]() ”》,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第113頁,中西書局2012年。
”》,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第113頁,中西書局2012年。
[4] 季旭昇:《說文新證》第517頁👨🏼🍼,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。
[5] 郭永秉、鄔可晶:《說“索”、“![]() ”》,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第103頁注3。
”》,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第103頁注3。
[6] 何琳儀🎀:《戰國文字通論(訂補)》第261頁,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。
[7] 施謝捷:《釋“索”》🐮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輯第202頁。
[8] 馬承源主編🍢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三)》第202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🏌️♂️。
[10] 張富海🧟🤵♀️:《漢人所謂古文研究》第79頁,線裝書局2008年。
[11] 裘錫圭主編,湖南省博物館🐤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富达編纂🛴: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》第4冊第121頁注22🙄,中華書局2014年✔️。
[12] 李守奎先生認爲這種寫法中間所從當釋爲“ ![]() ”🧑🏽🎄🕺,與“
”🧑🏽🎄🕺,與“ ![]() ”無關,同時認爲蔡侯器這類寫法與“
”無關,同時認爲蔡侯器這類寫法與“ ![]() ”没有直接联系。筆者以爲此說似無必要。李文見《清華簡〈系年〉中的“
”没有直接联系。筆者以爲此說似無必要。李文見《清華簡〈系年〉中的“ ![]() ”字與西申》,“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論壇——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”論文,中國社會科學院2012年🧘🏽♂️。正式發表於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七輯第168-177頁,商務印書館2014年👈🏻。另參見氏著👩🏽🔬:《清華簡〈系年〉中的
”字與西申》,“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論壇——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”論文,中國社會科學院2012年🧘🏽♂️。正式發表於《歷史語言學研究》第七輯第168-177頁,商務印書館2014年👈🏻。另參見氏著👩🏽🔬:《清華簡〈系年〉中的 ![]() 字與陳氏》🫁,第十九屆古文字年會散發論文🏄🏽♂️。
字與陳氏》🫁,第十九屆古文字年會散發論文🏄🏽♂️。
本文收稿日期爲2015年3月27日。
本文發佈日期爲2015年3月27日。
点击下载附件:
-

曰古氏 在 2015/4/10 13:15:09 评价道👨🏼🚒:第1楼
《繫年》文意明確,字形清晰,爲我們瞭解戰國文字構形提供了極佳的材料。如其中的“弃”字🚶♂️➡️,寫作筆畫不全的倒子形,或當是變體表意字,用身形不全的倒子來表示生子不舉👨🔬,故“弃”之👴🏻;又如“與”字,聲符“牙”或代換爲從“午”聲;……
Copyright 富达平台 - 注册即送,豪礼相随!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84952号 地址:富达注册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:200433
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
總訪問量:73886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