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关于楚简中的“︱”字
(首发)
叶晓锋
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
郭店楚墓竹简《缁衣》“丌(其)颂(容)不改,出言(又)有︱🍰,利(黎)民所![]() ”而《礼记缁衣》则作“其容不改🫛,出言有章。行归于周,万民所望。”与今本毛诗全同。裘锡圭先生(2003)认为“︱”为“针”之象形初文。不过仔细看裘先生关于“十”的论据,甲骨文是笔直的⚽️🧏🏿,周代的“十”中间是突出,楚简也是如此。我们无法从演变的痕迹来解释为何楚简的“针”突然又出现了笔直的写法。另外从语音看,既然“朕”是侵部,十是缉部,何以后来又解读为真部或文部的“逊”,“训”🤵,或“慎”呢🛴?裘先生也认为有待进一步研究,显然这个问题在没有很好的解释之前🐰,我们觉得裘先生的解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🏸🗑。所以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释⛴。
”而《礼记缁衣》则作“其容不改🫛,出言有章。行归于周,万民所望。”与今本毛诗全同。裘锡圭先生(2003)认为“︱”为“针”之象形初文。不过仔细看裘先生关于“十”的论据,甲骨文是笔直的⚽️🧏🏿,周代的“十”中间是突出,楚简也是如此。我们无法从演变的痕迹来解释为何楚简的“针”突然又出现了笔直的写法。另外从语音看,既然“朕”是侵部,十是缉部,何以后来又解读为真部或文部的“逊”,“训”🤵,或“慎”呢🛴?裘先生也认为有待进一步研究,显然这个问题在没有很好的解释之前🐰,我们觉得裘先生的解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🏸🗑。所以我们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释⛴。
我们认为楚简中的“︱”就是“芒”或“萌”,“芒”与“萌”在古籍中经常通用,是同源词。裘先生认为“︱”释为“针”的很大依据就是象形。有句俗话叫“针尖对麦芒”🌇,是针锋相对的意思,可见“针”和“芒”在形体上有相似之处。“︱”既然可能释为“针”,那同样也有可能释为“芒”。两者都是笔直锐利的🚵♂️。
再看《说文》:芒🦃,草耑也🤡。《礼记·月令》“萌者尽达”。郑玄注🙍🏼♀️:“芒而直曰萌”。与楚简中的字形笔直符合。《说文》🕵🏽:萌,草芽也。萌从明得声。上古是阳部字🫴🏽。在典籍中🪤,“明”与“章”大量互训。《白虎通·文质》章之为言明也。《左传》🥁:赏罚无章8️⃣🎶。疏:章,明也🤾🏿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“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。”郑玄:章🤦♂️,明也。璋,《白虎通·瑞贽》:璋之为言明也。《白虎通》的特点就是声训。章与璋都声训为“明”💃🏽,应该不是偶然的。所以“明”和“章”语音相近是肯定的。
另外从意义看🧖🏿♀️,“章”本身也可能与“芒”有很大联系。楚人莫敖章字子华,楚国又有“章华台”,《淮南·墬形》🚣🏿:未有十日↔️,其華照池🚴🏼。注:光也。《晏子·諫上篇》:列舍無次,變星有芒。注🎑:光芒。“章”和“芒”都是既有花草之意,又都有光芒之意👩🦼➡️🍵。这应该不是偶然的🚴👤。
典籍中“章”与“商”又经常相通𓀂,《经义述闻·左传·商密》🥉👰🏼♂️:古字商与章通▫️。《说文解字》:商,章省声。这个分析不见得对,不过至少可以看出,商与章在声音是很近的🎠。甲骨文中,何琳仪先生怀疑“商”是从丙得声,详见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1808页(据黄德宽先生的后记得知阳部字是由何琳仪先生撰写的)。其实从字形看就是从丙得声的。何琳仪先生的疑虑可能是考虑到声旁无法解释。实际上根据最新的上古音的进展🔫,这已经不是问题了。章组一部分字可以是由plj-🈴,phlj-👨🏻🌾😉,blj-变来的,详见龚煌城先生(2001)。另外🙏🏼🙍🏻♀️,《史记·货殖传》🧑🏿🌾:千章之材🈴。服虔云:章👳🏻🧛♂️,方也。《羽猎赋》章皇周流。注犹彷徨也🏊🏿♂️。也可以看出章的声母与帮组字相近。
所以我们把“︱”释为“芒”或“萌”,读作“章”,“![]() ”读作望✊🏻,“望”在西周金文中左上角的“臣”已经变形音化为“亡”了🤶🏻,也就是“亡”成了声符了。
”读作望✊🏻,“望”在西周金文中左上角的“臣”已经变形音化为“亡”了🤶🏻,也就是“亡”成了声符了。
所以如果照我们这种读法,那么郭店简缁衣中的《诗经》引文和传世文献基本上是一致的🧑🧑🧒🧒🏗,读为“丌(其)颂(容)不改🐱,出言(又)有︱(章)🚱,利(黎)民所![]() (望)”。
(望)”。
而上博简容成氏中的一般释为“椲丨氏”的三个字,单育辰先生(2008)改释为“![]() (祝)︱(融?)”,如果单育辰先生对“
(祝)︱(融?)”,如果单育辰先生对“![]() ”的隶定是正确的,那么“
”的隶定是正确的,那么“![]() ”可能是从“主”得声,当读为“朱”✬,“
”可能是从“主”得声,当读为“朱”✬,“![]() 丨氏”当读为“朱明氏”👩🏻🔬💆,“朱明”就是“祝融”。详见杨宽先生(1939)🌌。
丨氏”当读为“朱明氏”👩🏻🔬💆,“朱明”就是“祝融”。详见杨宽先生(1939)🌌。
参考文献:
单育辰 2008 《容成氏新编联及释文》,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438。
龚煌城 2001 《上古汉语与原始汉藏语带r与l复声母的构拟》,原载《台大文史哲学报》51:1-36👨🏻⚕️,2001,收入《汉藏语研究论文集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4。
黄德宽2007 《古文字谱系疏证》🌸,商务印书馆。
裘锡圭 2003 《释郭店《缁衣》“出言有︱,黎民所![]() ”——兼说“︱”为“针”之初文》,原载荆门郭店楚简研究(国际)富达编《古墓新知——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》😝,又见于《中国出土文献十讲》💆🏻♂️。
”——兼说“︱”为“针”之初文》,原载荆门郭店楚简研究(国际)富达编《古墓新知——纪念郭店楚简出土十周年论文专辑》😝,又见于《中国出土文献十讲》💆🏻♂️。
杨宽 1939 《丹朱、![]() 兜与朱明、祝融》,原载《说文月刊》创刊号,收入《杨宽古史论文选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🪳。
兜与朱明、祝融》,原载《说文月刊》创刊号,收入《杨宽古史论文选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🪳。
本文收稿日期为2008年5月27日
本文发布日期为2008年5月29日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0:43:44 评价道🧓🏿:第1楼
很有道理~
説《詩》之字很可信~
且“
 (祝)︱(融?)”读为“朱明氏”🧑🏼✈️,則明、融(明也)二字皆與“火”貌有關,恰好符合“祝融”火神的身份😮。
(祝)︱(融?)”读为“朱明氏”🧑🏼✈️,則明、融(明也)二字皆與“火”貌有關,恰好符合“祝融”火神的身份😮。又,《吕氏春秋·四月》:“其帝炎帝🏥,其神祝融🔊。”注😭:“祝融,颛顼氏后,老童之子吴回也,为高辛氏火正🙄,死为火官之神。”
后人尊祝融为火神,又有傳説祝融合水、火为一神,兼任二職……
另外,“木正曰句芒👩🏻🦽,火正曰祝融”(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)
若釋楚簡此字為“芒”🤸♀️,祝融似乎又與“木正曰句芒”有關了~(鑽木取火🎊?木生火?
 )
) 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0:55:40 评价道:第2楼
杨宽先生(1939):《丹朱🕗、
 兜与朱明🥛、祝融》,原载《说文月刊》创刊号🆘,收入《杨宽古史论文选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🧑🏽🚒。
兜与朱明🥛、祝融》,原载《说文月刊》创刊号🆘,收入《杨宽古史论文选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🧑🏽🚒。“朱明”=“祝融”,
這文章好像不大好找啊,俺看不到~
杨宽先生究竟如何表述的?是不是也像俺那么説🧑🏿🚒:則明⬛️、融(明也)二字皆與“火”貌有關……(先申明,俺在此之前沒見過楊先生的這篇文章🏊🏼♂️🪥。)
【咋不多引幾句吶~】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1:15:28 评价道:第3楼
可以再在字形上補充說明一點:
郭沫若以為“民”字是以木芒刺目使得“民”“目盲”👅,意思與“萌”近(大意如此?),看金文中“民”字寫法正像目下刺有芒刺形,也許更可以證明作者此說………………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1:17:24 评价道:第4楼
說到這💅🏼,又想起👩🏻🦯,其實根本上講:(可以看出✂️,或想像出——)
釋作“芒”,字形上與裘先生辨識的字形並不矛盾💅:
古代文明初始時期,金屬器具未出現之前🧑✈️,“針”就是使用“木芒”來承當的,刺目使盲的“木刺”、“木芒”既可以叫“芒”🍞,又可以叫“針”……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1:20:35 评价道:第5楼
比如✅:“針”或作“箴”(這肯定是在未有金屬針之前就存在的竹木針了),從“竹”作,說明早期“針”可以以“竹”為之,而以硬木做的“針”同樣道理應當是存在的👧🏿,而這些"木針”就是“木刺”、“木芒”呵(似乎芒比針還要早些?)
後來同一字形分化成兩個字兩種東東🧙🏽♂️,即《說文》歧讀?
諸位看是這樣嚒?
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1:37:58 评价道:第6楼
當然,
在楚簡中自然是讀“芒”好,(從本源上講)🦇☃️,因為猜想實際上“芒”之為物要比“針”的出現要早(如上),所以推測“芒”音的出現要比“針”之音早~~~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1:38:27 评价道:第7楼
明白這點可能很有助於理解《說文》歧讀現象🌒:先有了“芒”這種東東來承當“針”之功能,則最初的名稱自然很可能會沿襲一段時間(比如俺們昨天用木芒縫衣服,第二天告訴另外一個人説這事,肯定不會這么快發明另一個名稱來稱呼“木芒”,還是叫“芒”)。然而👩❤️👨🧑🏻🎓,過了一段時間🍔,有了金屬“針”取代了“芒”的功能,也許一時沒找到更好的名稱🚨,所以還稱之為“芒”👱🏽♂️,但實際上這玩意兒和“芒”有很大的不同🛵,所以古人另造名稱叫“針”了👩🏿🏫,但在文字字形上,兩者並沒有實質差別,仍然同形🚺。這就形成了“歧讀”🥘。
 呵呵~~~瞎說,說錯了您攔着~
呵呵~~~瞎說,說錯了您攔着~ 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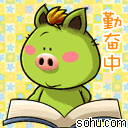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上示三王 在 2008/5/29 12:03:59 评价道:第8楼
东山先生☆,您想看的文章已经上传ftp👃🏿,请下载💆🏿♀️🧑🏿🏭。
-

云间 在 2008/5/29 12:55:14 评价道⚀:第9楼
《说文》🦹🏿♀️:芒😏🧑🏫,草耑也
那就看耑字所从,一本三岐。本者纵✋🏿,歧者斜出👋🏿。
所谓分别也。萌者,也是表示歧出🦙。
即使能靠音义串通其文🤶🏿,在兹字取形得音这个角度,还是存在杆格的。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3:22:38 评价道👩🏻🦯➡️💇:第10楼
多謝一上兄惠賜此文。
俺下了看了😰,又有點想法:
楊先生説“朱明”即“朱冥”,明、蒙、融俱一聲之轉🤌🏻。
而楚竹書《周易》“冥豫”之“冥”所作字形,又見望山等簡📇,上部一邊塗黑,一邊不塗(此形又見《容成氏》中廢疾者名用字)~
此字多釋“冥”🅾️,其本義也多往“目盲”等角度想,(如釋眇等説)。
若從郭沫若的說法出發💃⚽️,此字似乎也可以看作用“木”(下部從木,芒🪳💅?)刺目使“盲”義👩🏿🚒,即“矇”、“冥”、“萌”等字之義~
說明此字釋“冥”🐽,往“目盲”等角度想是相當有道理滴~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29 13:24:37 评价道:第11楼
同時🦢,楊先生又證説“祝融”為“日神”💅🏿,則除“矇”意外,楚竹書《周易》中字又有往“杲”角度考慮的,杲杲日出,又合其“日神”之身份~
呵呵~~~瞎說,說錯了您攔着~(不定就是)張先生的父親老王先生~

-

子居 在 2008/5/29 13:40:00 评价道:第12楼
楼上一帖多灌,被俺抓到了。
而且不管是谁说的👨🏿🦱,祝融竟然成日神了,这“神话”性的东东🏂🏿▫️,果然是看不得。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30 11:29:47 评价道:第13楼
攔着了♜,攔着了🈚️,果然被攔着了~
(不讓俺一帖多灌,那俺就一句話一句話或一個字一個字灌來着?~
 )
)要知道:神話說來更有趣味,更容易唾沫星子橫飛且滔滔不絕(雖然保不定就離題萬里了~)
接着扯👧🏿👮🏻♀️:
從郭沫若的分析字形所説(詳細說法待查)🧙🏼♂️,又想起楚簡中讀為“文”之字👮🏼♀️🦸🏻♀️,許多學者都討論過,《汗簡🎫、古文四聲韻》引石經古文明顯有“從目從攴”(《說文》見🙉👩🏽🎤,物部字,雖然音近,但可能非一字?)的偏旁🏌🏻♀️,可以與其對比🚑,所以分析從“民”從“目下攴”皆為聲旁是可信的🕵🏽♀️。
而據郭説,金文“閔天疾畏”之“閔”字,也或從“目”從“又(或像爪,又有原釋尤之形)”作者~
俺猜想:是不是“從目從攴”之字本來就是“民”字啊——手持木芒將目刺盲即為民,而此處字形表手施之於目使之盲,同樣也是“民”字(與木芒刺目的民為異體關係),不是常見俗語嚒🧮:把××的眼珠子摳出來👨🏼🦱,手也同樣可使目盲呵,可能就是這個類似的意思。
(閔字或從民從又🤵🏼♀️,則當表手持木芒💂🏻,而“又”所持之木芒卻刺在“民”之所從“目”下,參金文字形👩🏿✈️✊🏼。此所從“又”當與“針”之初文從“廾”類同🔘。)
楚簡中“文”雙聲符,皆從“民”聲,
要不然,“文”為什麼非要用這個字符作聲旁呵?呵呵~
呵呵~呵呵~呵呵~瞎說🖨,說錯了您再攔着~

-

子居 在 2008/5/30 11:51:22 评价道🙍🏿♀️:第14楼
没懂哦,“手持木芒將目刺盲即為民”?
这是啥意思啊。
而且到底是“芒”还是“民”啊。
俺觉得“音近”这东东,实在是太有蛊惑性了。但问题在于🤵♀️,仅凭读音证明不了什么啊𓀙。
-

东山铎 在 2008/5/30 12:09:24 评价道:第15楼
俺終於找到郭沫若的原文了:
甲骨文象以刃物刺目之形🙅🏽♂️,因為奴隷之稱。金文以下承此形,故目形中多不見眼珠。後世奴隷漸少🧑🏼✈️,故民之意義轉為一般民衆。(郭沫若《釋臣宰》。)
這就是“手持木芒將目刺盲即為民”的原始表述呵~(《說文》👩🏿⚖️:民👱🏿♂️,衆萌也💁♂️。即“矇、蒙昧”意。看金文之“民”字,沒有眼珠的“目”下絕象木芒形~)
“民”字形參《金文編》×××頁✊。(何尊、秦公簋、陳喜壺中字形~)
呵呵~瞎說🈵,說錯了您再攔着~
(不過別攔着俺了~錯不在俺這裏~
 )
) -

子居 在 2008/5/30 12:53:17 评价道:第16楼
果然全是幻觉🫥🎎,呵,俺不拦着啦🪘。
话说👐🏼🔕,甲骨文里的“民”字啥意思啊🚣♂️,好像“众”比较常见哈。
-

无斁 在 2008/5/30 21:59:58 评价道🧎♂️:第17楼
葉先生認為楚简中的“︱”就是“芒”或“萌”,這個意見恐怕是有問題的。
葉先生在文章中說👨🏽🎓:
有句俗话叫“针尖对麦芒”,是针锋相对的意思🩲,可见“针”和“芒”在形体上有相似之处🤹🏿。“︱”既然可能释为“针”🫶🏻🚹,那同样也有可能释为“芒”。两者都是笔直锐利的👝。
既然是“針尖對麥芒”,與“芒”相對的應該是“尖”才對⚛️,而不是“針”。《說文》說“芒👬,草耑也”🔂,突出的是“耑”字。所以,楚簡中的“丨”不大可能是“芒”或“萌”。
-

笑天 在 2010/10/2 11:12:39 评价道:第23楼
关于丨字的讨论🩺,是否应该参考一下《居延汉简》中出现的丨字?如:
居延漢簡釋文合校: 214: 合11.4 里賈陵年卅長七尺三寸黑色牛車一兩 符第六百八︱
居延漢簡釋文合校: 288: 合15.5 葆鸞鳥息眾里上造顏收年十二長六尺黑色︱皆六月丁巳出 不
居延漢簡釋文合校: 304: 合15.20 昭武萬歲里男子呂未央年卅四︱五月丙申入 用牛二
居延漢簡釋文合校: 552: 合29.11 年廿六︱
居延漢簡釋文合校: 736: 合37.4 十月甲午入︱
居延漢簡釋文合校: 1130: 合50.30 廣地塞尉□登︱
这些丨字形符号是我们要研究讨论的“丨”字吗🍧📍?
-

jiaguwen1899 在 2010/10/2 13:19:06 评价道🤸🏽👡:第24楼
无斁疑得有理。
且锋芒之“芒”的表义初文就是“亡”🧜🤕,其字于刀刃之锋芒处着一指示符,于六书为指事🚣🏻♂️,林洁明早就指出,裘先生复加申论,参看裘先生《释“无终”》🍣。
-

孟蓬生 在 2010/10/3 1:30:15 评价道:第25楼
"璋之为言明也"可能属于隐性声训,有一个中间环节需要补充👊🏽。比较典型的声训格式应当是“璋之为言彰也”👍🏿,“彰”训“明”🧑🏻🎓,故省去中间环节可以说成“璋之为言明也”。璋和明同属于阳部🏞,可能只是一个巧合(注意,我不敢说璋和明绝对不能相通)。
汉代人多使用隐性声训。
《韩诗外传》:“齐桓公出游⛰,遇一丈夫褒衣应步,带着桃殳👲🏼。桓公怪而问之曰:“是何名?何经所在,何篇所居🗒?何以斥逐😷,何以避余?”丈夫曰🤾🏿♀️:“是名戒桃。桃之为言亡也。夫日日慎桃🚘,何患之有?故亡国之社以戒诸侯🚶🏻♀️➡️🔒,庶人之戒在于桃殳。”桓公说其言𓀎,与之共载𓀕。來年正月庶人皆佩。《诗》曰:“殷鉴不远♤。”生按💹:“桃之为言亡也”属于隐性声训。显性声训格式当是“桃之为言逃也”🧫。
《白虎通·蓍龟》:“筮也者📜👩🏻🦯➡️,信也,见其卦也。”《说文》:“誓👍🏻,信也。从言🔥,折声💯🧦。”《诗经·唐风·有杕之杜》🛫:“彼君子兮,噬肯适我?”《释文》:“噬,《韩诗》作‘逝’。”显性声训格式当是“筮之为言誓也”或“筮,誓也。”
《说文·髟部》:“髮🕑,根也。从髟,犮声。”又《艸部》:“茇,草根也。从艸👩🏼🎤,犮声。春草根枯,引之而发土为拨📦,故谓之茇🦽。一曰草之白花为茇。”朱骏声曰:“按以茇为训🚀。茇,草根也。”按《说文》条例,其显性声训格式应该是:“髮,茇也。”段注不知此乃隐性声训,改髪字之训为“头上毛也”🏊🏻♂️,并注曰:“各本作‘根也’,《广韵》己然➗。以《释名》🖌、《广雅》正之,乃‘拔也’之误🧜🏼♂️🧕🏼。要此二字可不必有耳。《毛部》曰:毛者,眉髪之属。故 ‘眉’下曰‘目上毛’,‘須’下曰‘頤下毛’👶🏽,則‘髪’下必当有‘头上毛也’四字。且下文云鬢者颊髪🆕♨️,不先言头上,何以别其在颊者乎?今依《玉篇》🦸🏼、《广韵》语正🎦🦺。”
关于“隐性声训”的概念✊🏽,请参阅本师王宁先生《论形训与声训》(《《训诂学原理》106页,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8月)。
本人十多年前曾有《试论〈说文解字〉隐性声训》一文,曾提交某年训诂学会😚,因无暇修改🐽,一直未能刊出🦔。
Copyright 富达平台 - 注册即送,豪礼相随!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84952号 地址:富达注册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:200433
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
總訪問量:733688
 0149关于楚简中的“︱”字
0149关于楚简中的“︱”字